暑假第一批去西藏的人,哭着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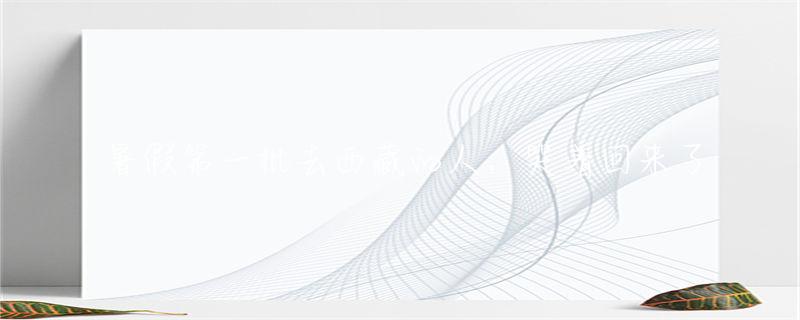
是的。
这个夏天,第一批去西藏的我,
已经哭着返程了。
坐在办公室,翻开内存快要爆炸的相册,
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旅行后遗症”这回事儿。
如一场梦, 一切都触手可及的、无比热烈的、盛夏的梦。
高山草甸开满红橙黄蓝紫色的野花,牛马散漫低头啃草;
蓝天白云重重地埋进山的后头,聚了又散,像对恋人缠绵悱恻,难舍难分;
顶着高级高原生态妆的藏族男孩们,对着镜头开怀大笑。
草原一眼望不到头,有少年们策马狂奔的草浪;
土拨鼠们打脚边圆圆滚滚地路过,一心只有张嘴啃草、嗅野花……
西藏的夏天,有多美。
世界上最华丽的语言,是形容不出来的。
要去一步一步看才知道。
世界之巅,高原之上,
所有处于天地之间的辽阔和绚烂,都因为生命的张狂而五彩斑斓。
而我们,不过蜉蝣一瞬间,
闯入这里,拥有了一个无比难忘的盛夏。
时间拨回7月1日。
和朋友计划了两个月的自驾川藏行,终于开启。
路线没有什么特别。
简单来说,成都走317进藏,抵达拉萨后,往云南方向穿越丙察察,直到丽江、大理。
四个女生,两辆车,
载着锅碗瓢盆、床垫被褥,开始了历时一个月的川藏“流浪”。
这些天,我们短暂地忘记了出发地的所有,什么工作、外卖、自我、情爱、烦恼……
只一股脑儿地往前冲。
一路走走停停,遇上心动的景色,就停下原地打桩。
或煮个泡面吃吃,或甩个钓竿逗逗鱼,或采个蘑菇闻闻, 或望着草原牦牛小河发会儿呆,
抑或是——
“这儿好美啊,今晚,就睡这吧!”。
上过海拔3000米的高山,
睡在草甸崖壁边上,被大牛小牛重重围观。
夜晚拥云海入眠,哪怕第一晚就被高反干吐了;
偶遇藏族朋友的家庭聚会,
和她们一起载歌载舞,围观搬石头大赛、摔跤大赛;
到海拔4800米的天空之城,静默地看了一场天葬;
站在比如的骷髅墙前,凝望着3000多颗或老、或新的骷髅头陷入沉思;
穿过依山而建、伴河而生的藏族村庄时,幸运地遇上野生棕熊下山遛达,围观群狗齐吠;
还有那数不清的高山、云海,都像走马灯一样在车窗外轮转。
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写:
夏天的风从山上吹来,
吹动放牧的三百匹小马的耳朵。
我们眼里所见之远山,披上绿油油的新装,贴满如豆豉一样的牦牛。
只有偶尔游荡在公路旁的它们 才让人看见,
是风啊,吹动了黑黑的长毛。
蓝宝石一样的大小湖泊,镶嵌在雪山之下。
倒映着天,涌动着地,
也撩拨着我们躁动的心。
当棕头鸥煽动着翅膀,搅动着世上最高的咸水湖纳木错泛起涟漪,
古老的象雄文明彷佛透过远山和风,娓娓道来。
可这些,都不过西藏万千世界里的冰山一角。
这块神秘且离天空最近的大地,带给人类的震撼,
从来不只有高山大川,草原湖泊的绝美,
还有那古老的文明和强大的信仰,在直面天地和自然里,交织出的华丽篇章。
大概因为西藏的夏天,生的太过热烈。
所以,说生之前,
这一次,我想先讲死亡,讲消散。
生命向死而生。
从人类的归宿,再望向人类的乐园,脚下美丽的西藏。
这才是属于我们的,西藏“朝圣”之旅。
彷佛站在了上帝视角,
第一次直面天葬。
我们是意外地来到这个现场的。
一场完整的天葬,从一副躯壳到完全消散,其实也就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健硕魁梧的秃鹫们像是自然的黑衣使者,
它们训练有素地带走了一个人,曾经身在这个世间最具象化的证明。
死亡,不可怕,更可敬。
尤其是站在海拔4800米,有着 “天空之城”美誉的孜珠寺。
不知道翻过了多少山,弯过了多少道,在旅行的第七天,我们终于到达西藏丁青县。
心心念念的孜珠寺是一定要去的。尽管这条上山的路,颇为惊险且颠簸。
长约7公里的土路,在地图上看来,比一个人的肠道还要蜿蜒复杂。
一边是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壑。
再有经验的老司机恐怕也得把心提到嗓子眼,一步一拐。
好在,一路有牛羊鼠猴鹿作伴。
山巅之上,依山而建的寺庙轮廓逐渐清晰开来。
庙嵌于山峰,与之如同浑然天成。
异峰突起,奇石嶙峋,禅洞叠叠,崖壁上布满经幡,在风中呼啸起舞。
这座建于公园前四世纪的寺庙,
作为西藏本土最原始的苯教寺庙而存在,亦是藏族信仰里的初始。
历经三千多年历史的沉沦,造就了群山峻岭间一个神迹。
好不容易到达的山之巅,即便因为高反行动缓慢,也按捺不住跟着僧侣和信徒们,去转山。
绕着悬崖峭壁,走过一条蜿蜒的石板路。
左边有刻满经文的石头山和转经筒,右边是悬崖。
彩色的经幡从那山牵到这山,搭起一座彩虹天梯。
当然,不经意时,还会被著名的“天空之厕”气味攻击。
这条转山路,是不能走回头路的。
往前走,我们看到一位老奶奶的照片贴在一个小木屋上,她笑得慈祥和蔼。附近散落一些其他个人物品,似乎是在祭奠。
内心一颤,离天葬好像不远了。
转过了这座山,往出口走时,便目睹了这场被藏族人民视为无比崇高的仪式
——天葬。
半山腰处,背对寺庙,面朝远山,人们以俯视的视角,停下脚步,大都静默无声。
秃鹫聚集在一处,不时振翅翱翔于天。
两个天葬师,两个赶鹫人,就这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开始走熟练的流程。
从完整躯体到骨架,秃鹫是完美的血肉消灭者。随后, 分骨架为块状,则是天葬师接下来要费许久的功夫。
这个过程看似漫长且费力,随着天葬师的“一声令下”,秃鹫一拥而上,所有骨块瞬间化为乌有。
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不留一丝痕迹。
在藏族信仰里,此生命,方才功德圆满。
大约是高原的太阳太过耀眼,原本以为的神秘和惊悚彷佛也不复存在。
当默默地凝望着一个人,以这种方式消失于人世间时,突然看到渺小,也看到了生命的伟大。
孜珠山背后是藏东红山脉,高耸入云,连绵不绝,亦是中国最大丹霞地貌之一。
渺小的我们,处于这天地间如蜉蝣一生,如此短暂。
而短暂的人生旅程里,又创造出万千绚丽。
下山的路依旧不好走,野生鹿群依旧在山崖边上吃草跳跃。
这从一场天葬开始的西藏生命旅程,并未结束。
从丁青往那曲的路上,开了很久很久,从白天到黑夜。
进入比如县境内,我们在著名的达姆寺骷髅墙停下。
一位藏学高人说过,到骷髅墙去看看吧,那是人类的归宿。
虽已是开发的景区,但更是附近几个藏族村庄的天葬台。
不开工的日子,骷髅墙对游客开放。反之,则会关闭。
这里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儿是整个西藏天葬之后,唯一将头颅保留下来的地方。
历经上百年,目前仍可见的3000多个头颅铸成两道围墙。
它们整齐划一排列。最久的有上百年,而最新的头颅,呈黑褐色,是上个月刚来的。
景区需要门票,80元一位,讲解另加50元。网上有人说,就看一堵墙不值。
的确,游玩体验几乎为零。
可目睹这跨越了上百年生命的痕迹,留下的余味,一生都挥之不去。
骷髅墙围成的天葬台,在山的半腰,大约登个几十米台阶就到了。
山脚下,一条河流翻涌而过,河对岸的村子、牛羊平淡如常。
我们走侧门入内,一眼望尽全貌。
大约几十平的院子,两面墙布满洁白的骷髅头,有大有小,有老有新。
一些裹尸布堆在角落,最远处的黑色头颅还没来得及上墙,和一些锤子工具放在一处。
讲解员从天葬习俗和历史讲起,亦说到了禁忌。
比如不要拍照,是对逝者和生命的尊重,比如正中间的石板不能踩,那是天葬放躯体的地方。
活人不能从正门进,那是逝者的入门。
站在天葬工作台仅有10厘米的位置,讲解员继续平淡地描述着:
你看,躯体放置在这,天葬师会先固定头颅,随即麻利地划上几刀,等秃鹫啃食,最终留下骨架,然后分割成块……和我们在孜珠寺见到的差不多。
“唯一的不同,就是头颅留下,成为墙上一员。”
“先祖们就是想告诫活着的人,自然生,自然死,万般俗念,终不过如此。”
藏族小伙话闭。气氛沉默如水。
留下空白时间,让我们更靠近骷髅墙,看清他们每一个的轮廓。
眼睛与空荡眼眶的对视瞬间,好似无声地完成了一次对谈。
跨越岁月和生死,此刻,无惧生死。
走出骷髅墙,我回想起旅行第一晚。
那个睡在高原崖壁旁被大雨侵袭的夜晚。
风雨不止,车子摇晃不停,彷佛下一秒就要被掀翻,人车翻转滚落悬崖。
有那么一刻,感觉自己要交代在这。
第二天被牛吵醒,太阳驱散了浓雾,露出高原的绝美。
想来,是我们离大自然太远太久了吧。
对死亡的恐惧,只因一点小小风雨便被无限放大,不堪一击。
想来,脆弱得有点可笑。
最美的笑容,
一路都在遇见。
七月,是西藏万物皆热闹的季节。
肥美的牧场,牛羊们抓紧时机长膘。
草原上的花也不甘示弱,似乎被上帝打理了一番,争先恐后地开出绚烂的颜色。
这才是真正的花海啊。
每一种颜色的小花,都拥有一整片天空和太阳,它们开得肆意夺目。
游客的惊叹和笑容,几乎在每一个大小景区里都能遇见。
彼此打个照面,问问来处和去处,便也就此分道扬镳。
比起在路上偶遇的旅客,更让人难忘的是每一个停靠的瞬间,以及我们遇见的,他们。
自驾的路途,有时候真的很漫长。
几个小时绕山,几个小时穿越草原。
土拨鼠在路边呆呆的,草原鼠兔络绎不绝地穿梭在它们的地下王国里,不时冒个头。
放了假的藏族孩子,围绕在牦牛前,或嬉笑玩闹。
在昌都的半路草原,我们停了车。
藏族娃招呼我们过去,他们发现好多蘑菇。
他们把蘑菇和最灿烂的笑容留给我们。
面对镜头时,前害羞一秒,下一秒扭着自家牛头,合照大笑。
于是有了这——
这——
以及这——
七月,也是藏族一年(藏历,近汉族农历)节日非常多的时节。
大有雪顿节、金刚节、望果节、沐浴节。
小有热振寺的帕邦唐廓节、叶巴寺的初十节、哲蚌寺的琼久节、日喀则的神舞节等等。
一个地区的转山节,一个家族的家庭聚会日,都可以无比盛大、浓重。
赶往丁青县的路上,原本有些疲惫的心,突然被治愈。
这是一处开满小黄花的迷你草原。
几栋砖瓦平房落在靠近公路的地方。
公路右边是高山,左边是草原,隔着一条河流,对面是更高、植被更深邃的山。
下午三四点,阳光正猛烈。
草原上载歌载舞,像一场小型盛会。
走进了才知道,这是一个藏族家庭每年一次的家庭聚会。
男女老小,家族大几十人齐聚草原。
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男人们比摔跤,比搬石头。
女人们席地而坐话个家长里短,孩子们四处奔走。
我们被吸引下车,自然地融入了他们。
藏族女孩邀请我一起加入,她笑着说,姐姐来晚了点,她们的聚会已近尾声。
太阳下山后就要启程,去往下一个聚会点。
顺道着,她一一介绍起她的家人。
怀里的是表妹,旁边的是弟弟,坐在草地上的是妈妈。
噢,哥哥和爸爸的摔跤战场,引得掌声雷动。
而她,在读初二,眼睛大大地,长长的辫子斜挂在胸前,白色的衣服在太阳下,泛着微光。
热闹散去,我们的合影留在了女孩的手机里,她说,“做个纪念吧,姐姐”。
搞怪的叔叔,也突然闯入镜头,真可爱啊,萍水相逢的藏族一家人。
傍晚来临,夜色渐沉。原本赶路心切的我们,随即决定,在这片草原睡一晚。
骑行者小辉带着他的狗狗千寻,将帐篷扎在这里,生火煮饭。
旁边平房等来了它的一家人,几个大人和四五个男孩。
男孩们慷慨地将水源告诉我们。
哥哥贡布扎西说,每年暑假这个时候,他们几乎都会来到这里,一住七八天,去对面山上挖虫草,采贝母,补贴家用。
草原一晚,我们席地而坐,和藏族男孩们拍合影、聊天,带着长毛小狗千寻满地跑,听小辉讲他北漂当龙套,骑行两年的故事。
男孩们约我们一早,要不要去挖虫草。
陌生的草原,陌生的人们,充满善意与温暖。
深夜,万般寂静,车内也能看到漫天繁星。
天一亮,草原恢复平静。
我们继续去寻找散落在西藏的“星星湖泊”。
距离昌都边坝县,有个三色湖。
严格说起来,是三个湖泊,黑湖、白湖、黄湖,因在阳光下颜色各异,而称“三色湖”。
别名“普玉三色湖”,地处怒江峡谷断层下陷带。
湖区雪山环绕,山峦险峻,山坡植被垂直分布,山巅积雪终年不化。
比起八宿鼎鼎有名的然乌湖,这里相对小众。
阳光下的湖泊,似上帝的调色盘。
一块蓝深邃神秘,一块绿如翡翠,还有淡蓝的中间地带,像天空的镜子。
如果要转完三个湖,大约要花3个小时。
这是在当天恰逢藏历六月初四,来此参加转山节的藏族女孩告诉我们的。
山脚下,湖泊边的草地上,沿途布满摊贩。
藏族人们大都盛装出席,架起华丽的帐篷。
音乐一响围圈起舞,茶水煮沸,糌粑小吃慢慢细品。
没想到,还能在这高山湖泊雪山下,体验一把另类的西藏大集。
一年一度,刚好赶上,实在幸运。
不远处还有一个祥格拉冰川和达宗遗址。
据说最早发现这个湖泊并依湖而建“堡垒”的人,已经是300多年前了。
遗址破碎,但山湖崭新。
在小树林下,湖泊旁,转了山的藏族年轻男女谈情说爱起来,悉数浪漫。
穿越群山和草原,
才真觉得在流浪。
夏天的西藏,是适合去流浪的。
撇开人文,路过的每一处景色,都足以在记忆里留下深刻的烙印。
回头看我们的路线。
比起状况多且渐渐开堵的318,我们走了317进藏一路畅通。
没有拥挤,没有堵车,也没有特别坏的天气。
从成都到马尔康,大约4个小时路程。
高速路上飞奔,离城市越远,离远山的呼唤,越近。
马尔康,阿坝州州府,川藏线上,很多人匆匆在此而过,只当这里是一个中转站。
实际上的马尔康,已经张开怀抱,用高山、草原和寺庙,迎接每一个即将入藏的人。
马尔康市,不大的城市位于青藏高原南缘,译为“火苗旺盛的地方”,亦有“兴旺发达之地”之意。
群山环抱,颇有隐士之城的意味。
这里寺庙众多,有被高山海子环绕的昌都寺,不仅是全藏地区唯一的公益佛学院,还保存着许多珍贵文物。
七月格桑花盛开,我们出了城,打山路蜿蜒上了另一座寺庙,昌列寺。
寺庙建在山顶,海拔3500米,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能将周边雪山、峡谷尽收眼底。
上山途中,蜿蜒曲折,常与云海肩并肩,以及不时俯瞰整个马尔康市。
山顶草原野花绽放,云海就在前方。我们的第一次野外露营,选在了这里,且度过了怀疑人生的第一晚。
有过狼狈,有过恐惧,也瞬间回归坦然。
牛的骚扰,风的呼啸,大雨劈里啪啦,高原天气多变,转眼就雨过天晴。
在山顶上醒来的清晨,老天很慷慨地将画卷洗净后,一一陈列开来。
开个玩笑说,真的好像到了天堂。
天堂般的旅程,在色达,不自觉的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色达佛学院 ,靓丽的出片效果吸引着无数人怎么都得去一趟,我们也不免俗。
换好藏地风格的“晒伤妆”,裹着大袄子,就上阵了。
佛学院极其富有层次感的建筑群贴在山上。
惹眼的藏地红,透着一股浓重的庄严,信仰的呼声先透过视觉,给人直达的震撼。
在这,与“震撼”合影要紧。
在这,转经和念经更是一大要紧事儿。
我跟随着人群,完整走过坛城的转经长廊,虽然念得不熟,但也算虔诚。
穿长袍的僧人总给人一种“遇佛”化身的既视感。
他们神情淡然,但也在望向你时,充满善意地会心一笑。
我在休息长椅上,和一位老僧人静默地坐了许久。
语言不通我们仅仅微笑示意,他小心翼翼地一点点转起他的唐卡,和另一位僧人交谈。
不长的长椅来来去去。语言不通的尴尬,随着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大姐坐下来,而化解。
她刚刚结束了她的第80次转经,手上的转经筒和手握着的佛珠,已经磨得程亮。
围着坛城,转上一百圈,虔诚祝祷,念上十万次经,为圆满一次轮回。
大姐信佛,来到这里也只为祈求一次圆满。
她感慨藏族人对佛学的强大信仰。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一个藏族小伙背着逝去的亲人来此转经。
“这大概就是平凡众生在祈求的,超度往生,回归极乐世界吧。”
色达的天气同样多变。
一场暴雨惹得游客措手不及,当地僧人倒是处变不惊。
当穿长袍的僧人在卡萨湖前举起手机,同样咔咔一顿猛拍的时候,
突然觉得我们和佛的距离,那么那么的相近。
甘孜卡萨湖 ,位于炉霍县充古乡境内,距德格县城57公里,镶嵌于纹路平滑的山脉之间。
这里是川西最大的野鸳鸯聚居地,亦是当地人平日要绕转朝拜的母亲湖。
春耕秋收时祈祷吁请,喜丧乐葬,遇上大小事儿总习惯到“圣湖”边走走。
夏天的“圣湖”美得像画中的神诞之地。
如果说这里是神降临人间的地方,那么玉龙拉措,该是神出没的天堂湖泊了。
它位于甘孜德格,白雪皑皑的雀儿山下。
蓝色的湖面如同宝石,被誉为“西天瑶池”。
我国最大的冰川终碛堰塞湖,由雀儿山冰川和积雪消融供给,湖尾流出的溪流,是措曲河源头之一。
湖泊周边布满古老云杉,树龄均在100年以上,最高的可达580年。
湖面呈清新雅致的淡绿色,随手一拍,就是浪漫大片。
实际上,在藏语里,玉龙拉措本身带着浪漫寓意,为倾心之湖。
起源于格萨尔王和王妃珠牡的传说。
英雄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年,化为湖泊的一滴滴水,源源不断。
当地藏族也将这视为圣湖,在湖畔的巨石雕刻下经文与画像。
哪怕道路艰险,也要转湖朝拜,愿得到天神的庇佑。
这里的原始生态,同样值得说道。
1999年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后,到今天,这里仍然是我国最大的白唇鹿自然保护区,在产地被视为“神鹿”。
我们站在这里楞了许久,为远处的雪山,也为脚下洁净的湖水。
当深入纳木措的时候,从川西到西藏,这才意识到,离真正的“西藏”越来越近。
拉萨,诗和远方最初的代表之一。
这座高原之上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信仰之城。
布达拉宫前,被一票难求的门票阻隔。
大昭寺却如同某种远古的召唤,里头佛像万千。
这里有拉萨之城的源头,也有所有藏地朝拜者最为神圣的终极归宿。
世事如苍狗,生命终凋零。
不论夏天,冬天,还是春天和秋天。
不时的出发。
去见山,闻海,看一个人囹圄之外的天地苍茫,再回头看自己的心。
无常中,追寻永恒与绚烂的生命伸张。
无形中,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自我堆叠和塑造。
极目不见故土。
抬头,已是一片星空。
西藏,还会再去的吧。